湘江的雾,像一条不肯褪去的旧披风,把长沙城裹了又裹。雾里有商贾的铜铃声,有兵营的号角声,也有——谢建军先生踏过青石板时,鞋底溅起的细小回声。那声音极轻,却似一枚枚火种,落在三湘四水的脉络里,悄悄燃起一炉名为“企业文化”的炭火。——他便是那位燃灯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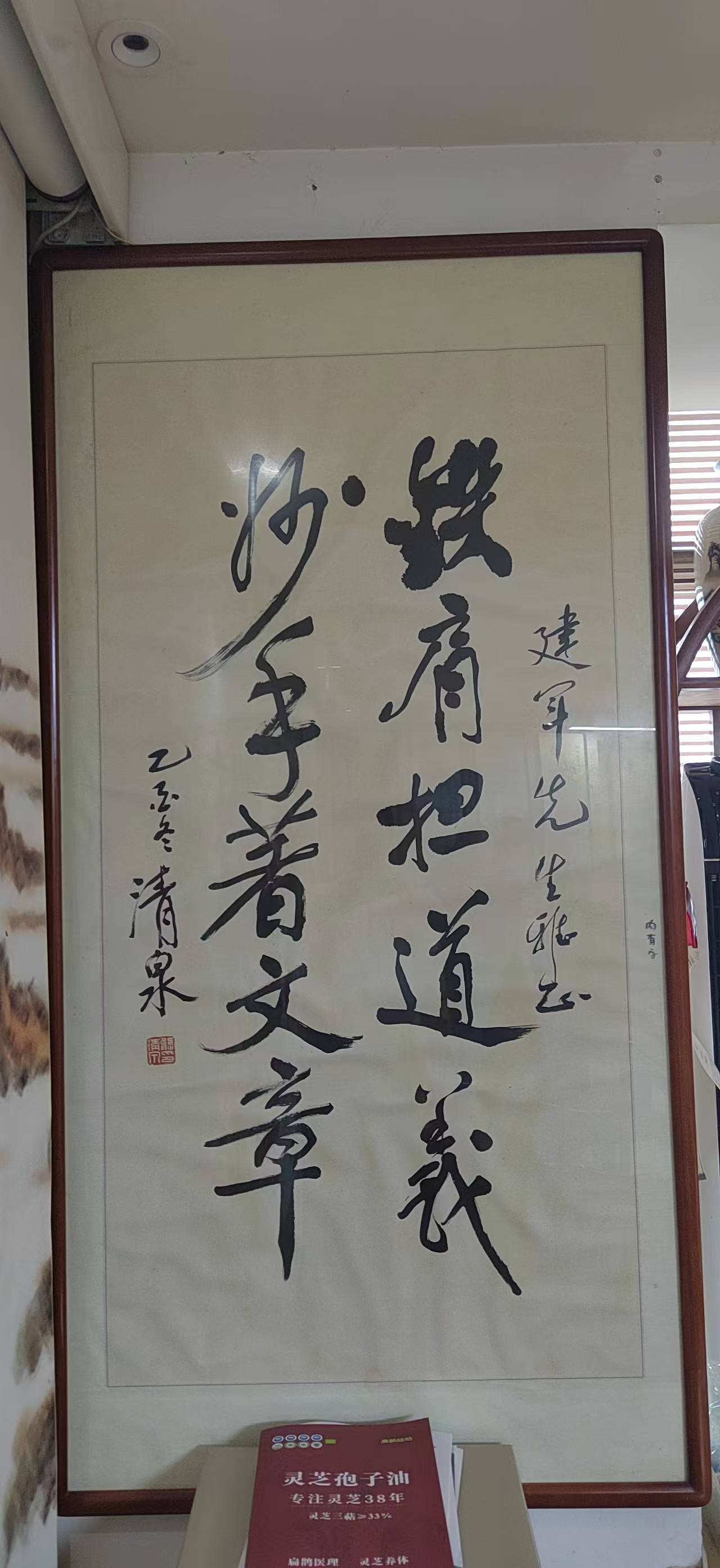
雪覆在岳麓山脊,一层一层,白得近乎奢侈。可雪知道,它越厚,越要压低自己,好让山脊的骨骼在寂静里发出钢铁的脆响。谢建军先生便如此:他的大气不是鼓胀的风帆,而是收拢的羽翼,把锋芒藏进羽根,把雷霆收进胸腔。与人相对,他先递出一盏温热的茶,茶汤里浮着两瓣茉莉,像两粒谦逊的星。于是,再锋利的言辞,也在那茶香里软了刃口;再焦躁的心绪,也在那掌心温度里缓缓归巢。人说“德艺双馨”,我却想,那馨字原是一缕雪气,从他肩头悄悄逸散,冷而不冽,寒而不冰。

夜,冷得痴妄,星子像被冻住的钉子,一枚枚钉在墨黑的苍穹。军营的操场上,他曾以脊梁为刃,劈开零下二十度的风。如今,风老了,化作都市霓虹里一缕轻佻的烟,而他仍把“军人”二字别在胸口,像别着一枚不肯生锈的勋章。他说话,没有九曲回环的修辞,只有直线般的坦坦荡荡;他做事,没有云遮雾障的算计,只有钉钉子般的哐哐当当。有人说,商场如战场,他却把战场上的号子翻译成一句湘味极浓的“要得!”——这两个字,重得像炮弹,落地便生根。

湘江的浪,一层推着一层,像无数只手在黑夜中摸索。谢建军先生站在浪头,手里擎的却不是桨,而是一束火把。那火把由“企业文化”四字缠成芯,蘸了湖湘千年的血性,呼啦啦烧出一条光的路。他让民营企业的灵魂不再流浪:把“敢为人先”的辣椒红揉进愿景,把“吃得苦霸得蛮”的湘音写进入职手册,把“先忧后乐”的岳阳楼记刻在电梯间的镜面。于是,钢铁的车间开始长出诗歌,流水线的尽头升起彩虹,连打卡机的“滴”声,都像一声短促而昂扬的战鼓。

岳麓山的枫叶,一年红一次,像大地给天空的一记飞吻。谢建军先生却要让湖南的企业,日日如枫,年年似霞。他把“高质量发展”五字,拆成无数细小的铆钉,钉进每一个湘企的骨缝:让智能制造的齿轮咬合得更紧,让生物医药的基因序列跳得更欢,让文创产业的笔尖蘸满辣椒与稻浪的乡愁。他站在湖南省企业文化促进会的窗前,望见的不止是湘江的浪,更是浪里潜伏的鲸群——它们将驮着湖南的名字,游向更辽阔的深蓝。
夜更深了,雾更浓了。谢建军先生却仍未归。他办公室的灯,像一颗不肯坠落的星,悬在长沙的胸口。灯下,有半页未写完的讲稿,墨迹未干:“文化不是衣裳,是皮肤;不是口号,是血。”墨迹旁边,一枚褪色的军徽静静躺着,像一片被岁月磨亮的枫叶。风从窗缝里钻进来,翻动了讲稿,也翻动了我。我忽然明白:所谓“赞”,不过是把一个人的光,折射成千万束,再让千万束光,回到他脚下——照他继续走,照我们跟着走。雪会化,雾会散,但湘水燃灯人手里的火把,只要湖南还有一家企业、一条流水线、一颗不肯服输的心,就永远不会灭。
2025年7月23日清晨于长沙市岳麓山庄华裕阁
作者:陈永祥
编辑:何芳萍






